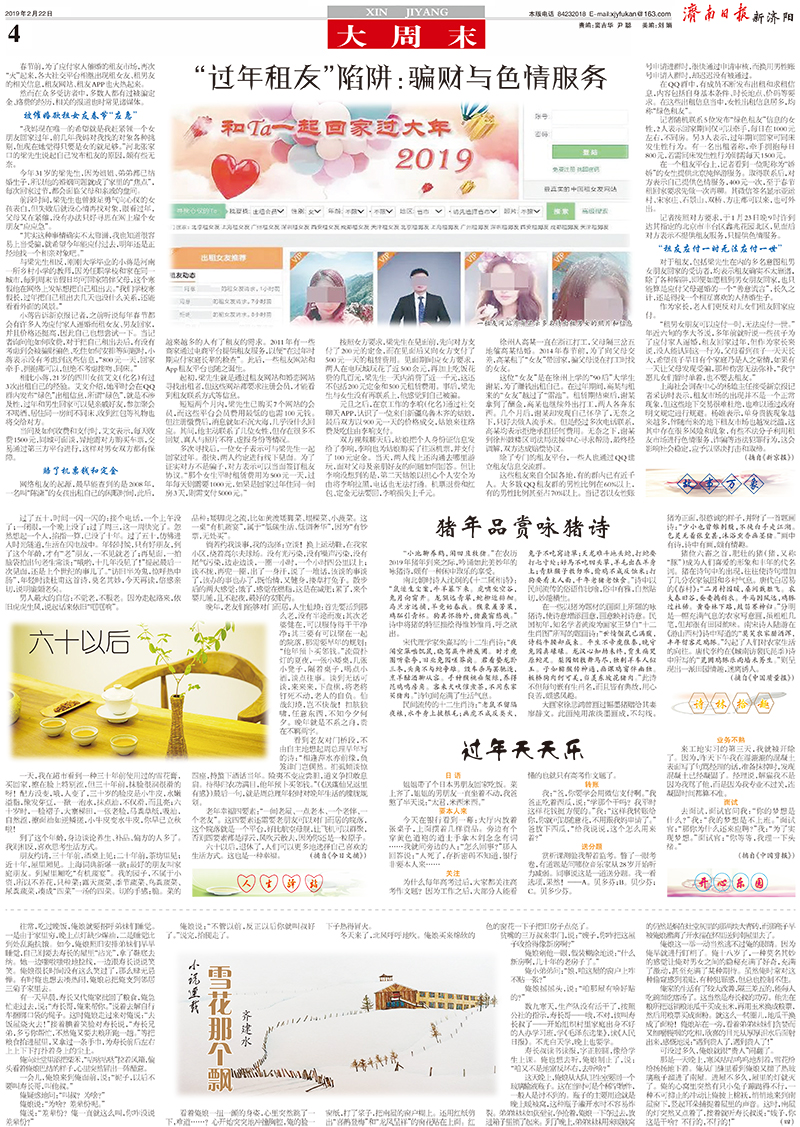小说连载:雪花那个飘
齐建水
往常,吃过晚饭,俺娘就要招呼弟妹们睡觉。一是由于家里穷,晚上点灯缺少煤油,二是睡觉比到处乱跑抗饿。如今,俺娘照旧安排弟妹们早早睡觉,自己则要去寿长的屋里“沾光”,拿了鞋底去纳。她一边嗤啦嗤啦地拉线,一边跟寿长说说笑笑。俺娘很长时间没有这么笑过了,那么肆无忌惮。有时俺也想去凑热闹,俺娘总把俺支到邻居三菊子家里去。
有一天早晨,寿长又代俺家批回了粮食,俺急忙走过去,说:“寿长哥,俺来帮你。”说着去解自行车捆绑口袋的绳子。这时俺娘走过来对俺说:“去饭屋烧火去!”接着腆着笑脸对寿长说,“寿长兄弟,多亏你帮忙,不然俺又要去粮所跑一趟。”等把粮食抬进屋里,又拿过一条手巾,为寿长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打扑着身上的尘土。
俺向灶堂里添把柴禾,“咕哒咕哒”拉着风箱,偏头看着俺娘巴结的样子,心里突然冒出一阵醋意。
一会儿,俺娘来到俺面前,说:“妮子,以后不要叫寿长哥,叫他叔。”
俺疑惑地问:“叫叔?为啥?”
俺娘说:“为啥?差辈份呢。”
俺说:“差辈份?俺一直就这么叫,你咋没说差辈份?”
俺娘说:“不管以前,反正以后你就叫叔好了。”说完,抬腿走了。
看着俺娘一扭一颤的身姿,心里突然跳了一下,难道……?心开始突突地冲撞胸腔,俺的脸一下子热得冒火。
冬天来了,北风呼呼地吹。俺娘买来绵软的窗纸,打了浆子,把南屋的窗户糊上。还用红纸剪出“喜鹊登梅”和“龙凤呈祥”的窗花贴在上面。红色的窗花一下子把旧房子点亮了。
贫嘴的三万叔来串门,说:“嫂子,你咋把这屋子收拾得像新房啊?”
俺娘剜他一眼,假装糊涂地说:“什么新房啊,几十年的老房子了。”
俺小弟弟问:“娘,咱这屋的窗户上咋不贴一张?”
俺娘摇摇头,说:“咱那屋有啥好贴的?”
数九寒天,生产队没有活干了,按照公社的指示,寿长哥——哦,不对,该叫寿长叔了——开始组织村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办学习班,学《毛泽东选集》,读《人民日报》。不光白天学,晚上也要学。
寿长叔读书读报,字正腔圆,像给学生上课。俺也想去听,俺娘制止了,说:“咱又不是地富反坏右,去听啥?”
这天晚上,俺娘从大队卫生室要回一个玻璃输液瓶子。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件,一般人是讨不到的。瓶子的主要用途就是晚上暖被窝,这种瓶子灌开水时不容易炸裂。弟弟妹妹如获至宝,争抢着,俺娘一下夺过去,放进箱子里锁了起来。到了晚上,弟弟妹妹用来暖被窝的仍然是焖在灶堂灰里的那两块大青砖,而那瓶子早被俺娘灌满了开水揣在怀里送到南屋里去了。
俺娘这一举一动当然逃不过俺的眼睛。因为俺早就进行盯梢了。俺十八岁了,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让俺对男女之间的隐秘充满了好奇,充满了激动,甚至充满了某种期待。虽然俺时常对这种偷窥感到羞耻,有种犯罪感,但总也控制不住。
俺家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,隔三差五的,能每人吃碗面疙瘩汤了。这当然是寿长叔的功劳。他先在粮所把返销粮地瓜干买成玉米,再用玉米换成粮票,然后用粮票买成面粉。就这么一转圈儿,地瓜干换成了面粉!俺娘站在一旁,看着弟弟妹妹们贪婪而又细嚼慢咽的吃相,欣喜的目光从厚厚泪水后面射出来,感慨地说:“遇到贵人了,遇到贵人了!”
可没过多久,俺娘就跟“贵人”闹翻了。
那是一天晚上,寒风咕咕呜呜地刮着,雪花纷纷扬扬地下着。俺从门缝里看到俺娘又揣了热玻璃瓶子溜进了南屋。进屋不多久,屋里的灯就灭了。俺的心窝里突然有只小兔子蹦跶得不行,一种不可抑止的冲动让俺披上棉袄,悄悄地来到南屋窗下,竖起耳朵捕捉着屋里的声音。这时,南屋的灯突然又点着了,接着就听寿长叔说:“嫂子,你这是干啥?不行的,不行的!” (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