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年记忆
李三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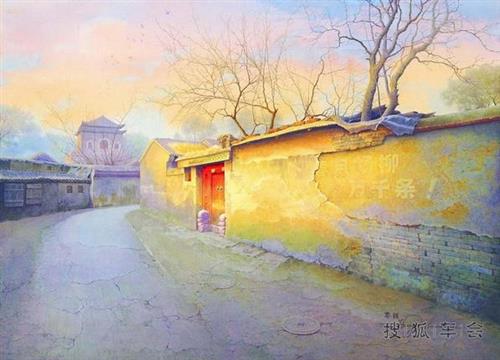
母亲病逝那年,我两周岁,也就是老家的习惯说法三虚岁,就像小曲儿唱的“小白菜儿心里黄,三岁的孩子没了娘!”可我竟没有丝毫丧母的悲痛记忆,甚至没有半点母亲的印象,没有照片,我终于也没有拼凑出母亲的样子,只是听说大姐长得像妈妈。我根本就不会叫妈妈,干妈非常疼爱我,我却从没当面喊过她,不是不想,是真的不会。好像我的童年词典里,根本没有“妈妈”二字。
没想到因为童年喊妈妈的语言功能的缺失,差点导致没人愿意做我的岳母。幸亏聪明的媳妇替我遮掩,厚道的岳母好像明白了原委,再加上我骨子里尊老爱老的秉性,很快赢得了老人的喜爱,直到去世,我和岳母亲如母子,但我终究也是没有当面喊她一声妈妈。
儿时的我,经常被周围的人小声议论“这就是那个三岁没妈的孩子!”但我好像真的没有感觉到相比同龄人的不幸,来自周围加倍的呵护时常各种方式温暖着我幼小的身心。至今,那历历温情就像一坛陈年老酒,不用开启,眯上眼睛想一下都能感觉到那股熟悉的醇香,而且随着年份增长,滋味儿愈来愈浓烈了。
干妈一家
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在家务农,但却不像普通庄稼人,他交往很广,远朋近友经常带我走走。我最喜欢去的,要数干妈家了。干爸和父亲是同学,社会运动之前是西安钢厂的保卫科干部,同样身不由己做了公社社员,两人同命相怜、无话不谈。干爸头脑灵活,利用家族在东北的关系,经常寻点政策的漏洞,倒腾木材或粮食,赚点差价补贴家用。还将我十九岁的大哥带到东北林场做了伐木工人,每年年底,大哥赚的钱父亲用来交给生产队购买一个劳动力全额工分,还会有所剩余。
干妈回乡之前是西安钢厂的财务人员,虽是四个孩子的母亲,但一直干净利落,讲话慢条斯理,我见过她和干爸年轻时坐着一条长凳的照片,干爸就像《红灯记》的剧照李玉和一样,带着大盖帽,威武英俊,干妈披肩发型,清秀的瓜子脸,怀里抱着他们第一个孩子。
干妈有台缝纫机,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绝对的稀罕物,时常会送我可身的衣服,很早就给我做了一个书包,底色是深蓝,两面分别用四种颜色的八个三角拼成一个方块,既漂亮又结实。
每当干爸和父亲天南地北、借酒谈心的时候,干妈总是一边接话聊天,一边做菜。她做的菜不光好吃,还好看,普通的鸡蛋,用盐水煮熟,将皮剥光,淡淡清香中略带咸味,每个平分四块,浇上姜汁和香油,就类似现在的“姜汁松花蛋”只是更加鲜亮,不用刀切,而是用缝纫机的细线勒开的。每做好一个菜,干妈都会喊我过来,轻轻坐下给我夹菜。每当此时,父亲总赶我出去玩,我也总是张嘴接住干妈送到嘴边的美味,然后转身飘出,汇合正在门口偷瞧的两个干兄弟出去疯一圈儿!
干妈趁着二人酒酣话密之际,做好菜出去了一会儿,领来一个端庄女人,干妈要我们三个喊她小姨,她们进屋聊了一根烟的功夫,那个女人便红着脸走了,干妈在后面送出。返回屋里,干妈数落父亲“你看你,把话说这么绝,弟妹走了三四年了,你才四十挂零,就这样过下去吗?人家比你小七八岁,里外一把手,为了侍奉多年瘫在炕上的老娘才耽搁到这么大的,现在老娘走了,无牵无挂,就想找个厚道有主见的人,这样的姑娘能和你一心一意过日子的。人家没嫌你孩子多,你咋还不同意呢?”“是呀,你到底咋想的?”干爸也两手捧着茶杯,盯着父亲问。
父亲端起酒杯一饮而尽,又深深地咽了一口茶水,然后平静地说“多谢大哥大嫂的好意,不是我不识抬举,人家是大闺女,以后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吗?现在的岁月,虽然不像六零年饿死人,但也就勉强填饱肚子,真要出现一碗水端不平的事情,要我咋办呢?我这几个孩子可就真落到后娘手里了!何况老大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,八字还没一撇呢!放心吧,这几个孩子我自己能拉扯大!”
干妈一家都很喜欢我,两个儿子一个大我一岁,一个小我一岁,争着和我拜把兄弟,军哥是对点儿的干哥,民弟是我俩的兄弟,我们仨最喜欢做的莫过于抓鱼煮鱼了。大寺河流经村西头,常年水流平稳,水草丰美,小鱼小虾成群结队。别看军哥才大我一岁,捕鱼捞虾样样精通,我和民弟非常崇拜。我负责在河堤上“埋锅”生火,沙土很松,挖好坑,两边用泥土垒起小墙,上面平放上一个铝制饭盒,里面加满河水,岸边杨树林下面有树叶树枝做柴禾。民弟当然是我俩的助手,一会儿被水里的军哥喊去捡拾鱼虾,一会儿被我打发回家“窃取”调料,当然他的屁股没少替我俩挨打。
干妈家还有两个大我十来岁的姐姐,荣姐和凤姐,两个人不像是农村孩子,既干净漂亮,又勤快懂礼,她俩经常骑一辆自行车来我家,接近二十里路,两人轮流蹬车,每次就住几天,她俩一来我家从内到外都会焕然一新,就连我家两位姐姐的辫子也会经常变换新奇的花样。
生产队也是家
我印象中,生产队的上工集合挺有趣儿。我家院内有棵茂密的臭椿树,一个粗大的树杈伸出院墙,上面吊着一整片铁铧犁的犁背,同样还垂吊着一个鸭梨型的小铁锤儿,铁锤儿下还系着一段绳头,人站在地上频繁扯动绳头,铁锤儿正好敲打在铁犁的中间部位,发出叮当清脆的声音,这就是我们队里上工集合铃声,每天上午下午队长都需要敲打三遍。队长敲完第一遍铃后,披着一件白褂子露着胸膛,摇着蒲扇,又慢慢踱步回家,父亲匆忙吃完饭安排好全家的事情,等第二遍铃声一响,他便出门,问清楚活计,然后回家取了工具返回院外,找个树荫坐下和大家聊天,此时包括队长大约三四个人,其中总会有木匠爷爷和父亲的。第三遍铃声响过,大部分社员才揉着眼睛打着哈气来到周围坐下,很快婶子大娘们飞针走线纳鞋底鞋帮的噌噌声,大叔大爷们借火点烟声,三五成群家长里短聊天声,还有队长提高嗓门分派工作声,五六十人呜呜呀呀!此时我经常骑在树上看下面的风景,每次都是被下面一股股旱烟味呛得下来。
队里管理还是很人性化的,干上一个时辰,要休息一会儿,女人们大多回家喂孩子,男人们抽个地头烟解解乏,父亲此时会快速在旁边割满一筐羊草,当时的田里,草比苗旺。
当然了,生产队里各项劳作的轻松,积累到秋天,收获就更轻松了。队里给粮所缴完爱国粮,会计算盘一响,场院里开始按照各家工分总额分配,小麦、玉米、地瓜、花生、大豆,有时加上几个冬瓜还满不了一个太平车。没有车子的,用肩挑,一家人全年的粮食轻轻松松搬回家。走亲访友坐下来前三句话肯定有“今年你们吃多少?”(意思是你们那里全年每人分多少粮食)我记得一次父亲回干爸说,那年我们队吃九斤小麦。
上面也有抓得很给力的事情,比如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,特别是工作组到来,都是拥有尚方宝剑的,权大无边,组长老王,披着一件威武的军大衣,一张黑黑的大脸甚是吓人,开会经常自称是铁面无私的包公。刚来时正赶上东坡地里丢了二十几个玉米棒子,他马上率领工作组全员还有四个民兵,将几个地富成分家庭翻了个底朝天,一无所获,最后查清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借割草时候掰回家的,幸亏他家是贫农,只是在全村游街示众一天,要换了地富子弟最少要判几年徒刑的。每当此时,父亲总会感激爷爷的先见之明,运动之前就主动散尽家财给村里需要帮助的乡亲,也使得我入学登记在“家庭成分”一栏可以自豪地填写“中农”。
平坟运动“包公老王”也做得雷厉风行。按照土地使用规划,各家要将祖坟迁入村里统一划定的墓地,限期完不成的,工作组强行平掉。一时间到处哭声雷动、纸钱飞扬,全村沉浸在出殡的气氛中,谁家没有几座祖坟呀!来不及或者买不起棺材的,大都用个门板,上面用秫秸和白纸扎一个棺材,儿女们一边啼哭着诉说着将先人的遗骨小心安放进去。有个给伪政权做过事情去世时间不是很久的人,墓穴扒开棺材乌黑锃亮!“包公老王”坚决不答应,“不能让反革命分子继续享受劳动人民的血汗”!他带头跃上棺材顶,将死人“赶走”,棺材拆解成板材,送给学校。后来我在学校见过,用很大的蓝砖垫起来,一年级孩子当课桌用。不久“包公老王”走了,听说因为作风问题。
缺吃少穿犯愁是大人的事情,我们小孩子那时还真是无忧无虑,即使上学了也没有家庭作业。春天爬树撸榆钱、拧柳笛,享受大自然的恩赐;夏天摸鱼虾、捉迷藏,一个个黑黝黝的透着健康;秋天放羊、割草,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队里果园瓜地也;冬天棉袄棉裤不怕脏,冰上撒欢抽陀忙。(一)
作者单位 济南大华塑料加工厂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