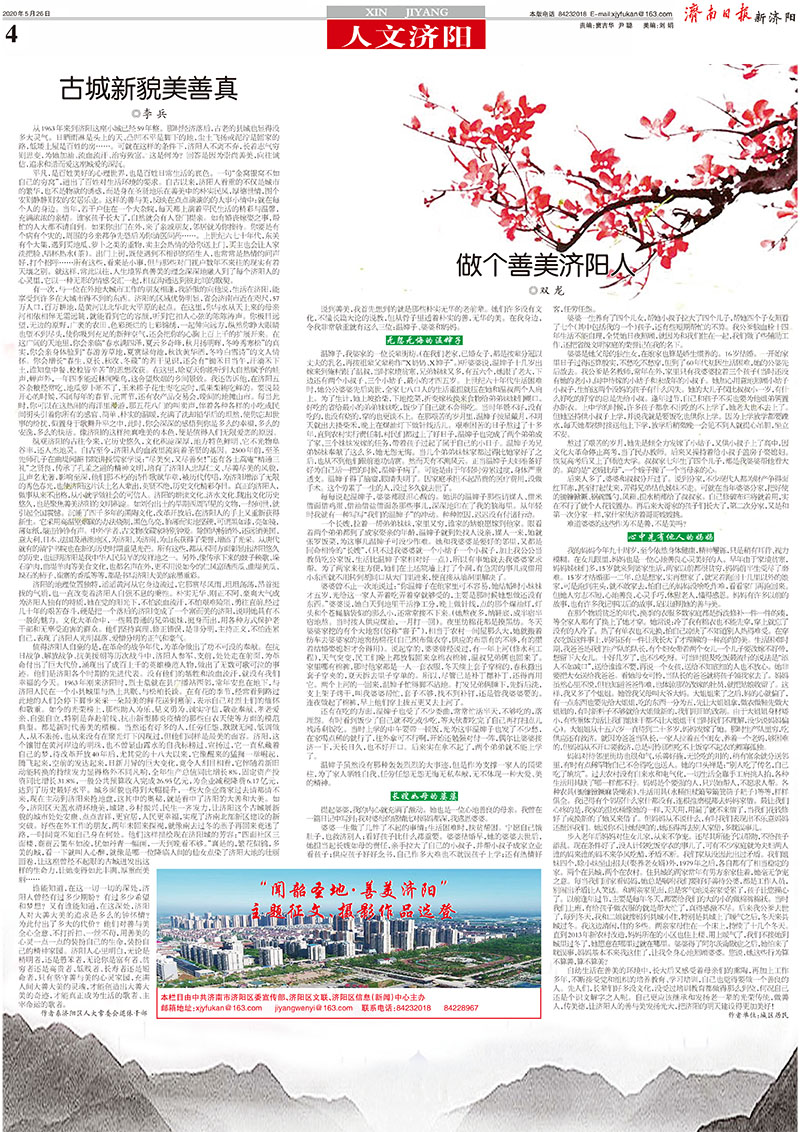做个善美济阳人
◎双 龙
说到善美,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朴实无华的老前辈。她们许多没有文化,不懂长篇大论的说教,但从骨子里透着朴实的善,无华的美。在我身边,令我非常敬重就有这么三位:温婶子、婆婆和妈妈。
无怨无悔的温婶子
温婶子,我婆家的一位长辈街坊。(在我们老家,已婚女子,都是按辈分冠以丈夫的乳名,再按祖辈父辈称作“X奶奶、X婶子”。)听婆婆说,温婶子十几岁出嫁来到俺村跟了温叔,当时家境贫寒,兄弟姊妹又多,有五六个,她跟了老大,下边还有两个小叔子、三个小姑子,最小的才四五岁。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,她公公婆婆先后离世,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就压在她和温叔两个人肩上。为了生计,她上坡拾柴,下地挖菜,折变嫁妆换来食物给弟弟妹妹们糊口。好吃的省给最小的弟弟妹妹吃,饭少了自己就不舍得吃。当时年景不好,没有吃的,也没有烧的,穿的也更谈不上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,温婶子披星戴月,不明天就出去搂柴禾,晚上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儿。艰难困苦的日子熬过了十多年,直到农村实行责任制,村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,温婶子也完成了两个弟弟成了家、三个妹妹发嫁的任务,带着孩子过起了属于自己的小日子。温婶子为兄弟姊妹奉献了这么多,她无怨无悔。当几个弟弟妹妹家都过得比她家好了之后,也从不到他们跟前邀功请赏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。正当温婶子夫妇准备好好为自己活一把的时候,温婶子病了。可能是由于年轻时劳累过度,身体严重透支。温婶子得了脑瘤,眼睛失明了。因家庭承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,没做手术。这个劳累了一生的人,没过多久就去世了。
每每说起温婶子,婆婆都眼泪心酸的。她讲的温婶子那些请媒人、借米借面借鸡蛋、借油借盐借面条那些事儿,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从年轻时我就有一种写写“我们的温婶子”的冲动。种种原因,迟迟没有付诸行动。
一个长嫂,拉着一帮弟弟妹妹,家里又穷,谁家的姑娘愿嫁到他家。眼看着两个弟弟都到了成家娶亲的年龄,温婶子就到处找人说亲,媒人一来,她就张罗饭菜,为这事儿温婶子可没少作难。她和我婆婆是要好的邻里,又都是同命相怜的“长嫂”,(只不过我婆婆就一个小姑子一个小叔子,加上我公公当教员吃公家饭,生活比温婶子家相对好一点),所以有事她就去我婆婆家求帮。为了两家来往方便,她们在土坯院墙上打了个洞,有急需的事儿或借用小东西就不用转到胡同口从大门里进来,便直接从墙洞里解决了。
婆婆曾不止一次地说过:“你温婶子在他家里可不容易,她结婚时小妹妹才五岁,光给这一家人弄着吃弄着穿就够受的,主要是那时候她想做还没有东西。”婆婆说,她白天到地里干活挣工分,晚上做针线,点的那个煤油灯,灯头和个苍蝇脑袋似的那么小,还常常接不下来。(她熬夜多,纳鞋底,成半宿半宿地熬。当时按人供应煤油,一月打一回)。夜里纺棉花都是摸黑纺。冬天婆婆家挖的有个大地窖(俗称“窨子”),相当于农村一间屋那么大,她就搬着纺车去婆婆家的地窖纺棉花(自己织布做衣穿,供应的布票有的不够,有的攒着结婚娶媳妇才舍得用)。说起穿的,婆婆曾经说过,有一年上河(修水利工程),天气突变,民工们晚上都放假回来拿棉衣棉裤,温叔兄弟俩也回来了。家里哪有棉裤,那时他家都是一人一套衣服,冬天续上套子穿棉的,春秋撤出套子穿夹的,夏天拆去里子穿单的。所以,尽管已是补丁摞补丁,还得再用它。两个上河的一回来,温婶子忙得脚不沾地。打发兄弟俩睡下,先拆后洗,支上架子烤干,叫我婆婆帮忙,套子不够,找不到补钉,还是管我婆婆要的。连夜做起了棉裤,早上他们穿上拔五更又去上河了。
还有在吃的方面,温婶子也受了不少委曲,常常忙活半天,不够吃的,落埋怨。有时看到饭少了自己就不吃或少吃,等大伙都吃完了自己再打扫点儿残汤剩饭吃。当时上学的中午要带一顿饭,光为这事温婶子也发了不少愁,在家喝点稀的就行了,往外拿可不行啊,开始还勉强对付一阵,偶尔让婆婆接济一下,天长日久,也不好开口。后来实在拿不起了,两个弟弟就不能上学了。
温婶子虽然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大事迹,但是作为支撑一家人的顶梁柱,为了家人牺牲自我、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无私奉献,无不体现一种大爱、美的精神。
长嫂如母的婆婆
提起婆婆,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激动。她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母亲。我曾在一篇日记中写到:我对婆母的感情比对妈妈都深,我感恩婆婆。
婆婆一生做了几件了不起的事情:生活困难时,扶贫帮困。宁愿自己饿肚子,也救济别人;看好孩子比什么都重要。婆婆结婚早,她的婆婆去世后,她担当起长嫂如母的责任,亲手拉大了自己的小叔子,并帮小叔子成家立业看孩子;供应孩子好好念书,自己作多大难也不耽误孩子上学;还有热情好客,任劳任怨。
婆婆一生养育了四个儿女,帮她小叔子拉大了四个儿子,帮她四个子女照看了七个(其中包括我的一个)孩子,还有些短期帮忙的不算。我公爹脑血栓十四年生活不能自理,全凭她日夜照顾,就因为和我们住在一起,我们做了些辅助工作,还把省级文明家庭的荣誉记在我的名下。
婆婆是她父母的独生女,在娘家也算是娇生惯养的。16岁结婚。一开始家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,不愁吃不愁穿,但到了60年代初因生活困难,她的公婆先后故去。我公爹是名教师,常年在外,家里只有我婆婆拉着三个孩子(当时还没有她的老小)、闺中待嫁的小姑子和未成年的小叔子。她加心用意地照顾小姑子小叔子,生怕这两个没妈的孩子有什么闪失。她的大儿子仅比叔叔小一岁,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总是先给小叔。逢年过节,自己和孩子不买也要为他姐弟俩置办新衣。上中学的时候,许多孩子都拿不出吃的不上学了,她老大也不去上了。但她坚持供小叔子上学,并说我就是要饭吃也供你上学。因为上学放学都要蹚水,每天她都按时接送他上下学,放学后稍微晚一会见不到人就提心吊胆,坐立不安。
熬过了艰苦的岁月,她先是倾全力发嫁了小姑子,又供小叔子上了高中,因文化大革命停止高考,当了民办教师。后来又操持着给小叔子盖房子娶媳妇。恢复高考后又上了师范大学。叔叔家七年生了四个儿子,都是我婆婆帮他看大的。真的是“老嫂比母”,一个嫂子操了一个当母亲的心。
后来人多了,婆婆和叔叔分开过了。说到分家,不少现代人都为财产争得面红耳赤,甚至打起仗来,弄得兄弟结仇姊妹不走。可就在当年婆婆分家,把好使的锄镰锨镢、锅碗瓢勺、风箱、担水梢都给了叔叔家。自己修破布烂将就着用,实在不行了就个人花钱置办。再后来大哥家的孩子们长大了,第二次分家,又是和第一次分家一样,家什家伙济着哥哥嫂嫂挑。
难道婆婆的这些作为不是善,不是美吗?
心中先有他人的妈妈
我的妈妈今年九十周岁,至今依然身体健康,精神矍铄,只是稍有耳背、视力模糊。在女儿眼里,妈妈也是一位心地善良心灵美好的人。早年由于家境贫寒,妈妈姊妹们多,15岁就来到婆家生活,两家以前都很贫穷,妈妈前半生受尽了磨难。15岁才结婚那一二年,总是想家,实再想家了,就哭着跑回十几里以外的娘家,可是跑到庄头,就不敢家去,怕自己的妈妈没啥吃作难,看看家门再跑回来。但她人穷志不短,心地善良,心灵手巧,体慰老人,懂得感恩。妈妈有许多以前的故事,也有许多我记事以后的故事,足以证明她的善与美。
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,换季的衣服多数家庭都是拆洗修补一件一件的凑,等全家人都有了换上了她才穿。她常说:冷了我有棉衣也不能先穿,穿上就忘了没有的人冷了。热了有单衣也不先换,怕自己凉快了不知道别人热得难受。在穿衣吃饭这件事上,妈妈还有一件让我长大了才理解的一种高尚的美。生活困难时期,我爸爸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,有个妇女带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要改嫁不好带,想留下大女儿。十好几岁了,也不少吃呀。可当时提及吃饭最流行的说法是“添人不如减口”,送给谁谁不要,再说一个女孩,送给不知底细的人也不放心。她非要把大女送给我爸爸。看她母女可怜,当队长的爸爸就将孩子领我家去了。妈妈虽然心里不悦,但也知道爸爸作难,也体谅那位改嫁的社员,就把姑娘收留了。这样,我又多了个姐姐。她管我父母叫大爷大妈。大姐姐来了之后,妈的心就偏了,有一点东西也要先给大姐姐,吃的东西一分为五,先让大姐姐拿,做衣做鞋先做大姐姐的,有时新料子不够就给大姐做新的,我们用旧的改制。由于大姐姐身材矮小,有些重体力活让我们姐妹干都不让大姐姐干(当时我们不理解,没少说妈妈偏心)。大姐姐从十五六岁一直待到二十多岁,妈妈发嫁了她。那时生产队里穷,吃供应还有救济。就因为爸爸当队长,一家人拉着五个闺女、养着一个老妈,够困难的,但妈妈从不开口要救济,总是可怜那些吃不上饭穿不起衣的鳏寡孤独。
妈妈对待邻里街坊也很和气,乐善好施,无论吃的用的,稍有富余就分送邻里,有时有点稀罕物自己不舍得吃也送人。她的口头禅是:“别人吃了传名,自己吃了填坑”。过去农村没有自来水和电气化,一切生活全靠手工肩挑人抬,各种生活用具缺了哪一样都不行。妈妈是个要强的人,只兴她帮人,不愿求人帮。各种农具(锄镰锨镢麻袋绳索)、生活用具(水桶担杖簸箩簸箕筛子耙子)等等,样样俱全。我记得有个邻居什么家什都没有,连根推磨棍都去妈妈家借。最让我们心疼的是,我家的担水桶像她的一样,天天用,用漏了就不来借了,当我们花钱修好了或换新的了她又来借了。但妈妈从不说什么,有时我们表现出不乐意妈妈还批评我们。她说你不让她使咱的,她还得再去别人家借,多耽误事儿。
步入老年后妈妈对住女儿家,从来不争宠。还尽其所能予以帮助,不给孩子添乱。现在条件好了,没人计较吃饭穿衣的事儿了,可有不少家庭就为夫妇两人谁的妈来谁的妈不来争风吃醋,矛盾不断。我们家从没因此出过矛盾。我们姐妹四个,除小妹坐山招夫(娶养老女婿)外,1979年之后,各自都有了相当稳定的家。两个在县城,两个在农村。住县城的两家常年有男方亲家住着,她毫无争宠之意。每当我们回家看妈妈,她总是嘱咐我们要好好善待公婆,都是工作人员,别闹出矛盾让人笑话。和两亲家见面,总是客气地说亲家受累了,孩子让您操心了。以前逢年过节,主要是每年冬天,都要给我们的大的小的做棉裤棉袄。当时我们上班,有给孩子做衣服的就是帮大忙了,真得感激不尽。后来我公爹去世了,每到冬天,我和二姐就接妈到县城小住,特别是县城上了暖气之后,冬天来县城过冬。我这边清闲,住的多些。两亲家母住在一个床上,持续了十几个冬天。直到2013年新农村改造,妈妈所在的小区也住上楼、用上暖气了,我们不接她到城里过冬了,她愿意在哪里过就在哪里。婆婆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之后,她怕来了耽误事,妈妈基本不来我这住了,让我全身心地照顾婆婆。您说,她这些行为算不算善,算不算美?
自幼生活在善美的环境中,长大后又感受着母亲们的熏陶,再加上工作多年,不断接受党和组织的培养教育、学习培训,自己也觉得要做一个善良的人。先人们,长辈们好多没文化,没受过培训教育都做得那么到位,何况自己还是个识文解字之人呢。自己更应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,做善人,传美德,让济阳人的善与美发扬光大,把济阳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!作者单位:城区居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