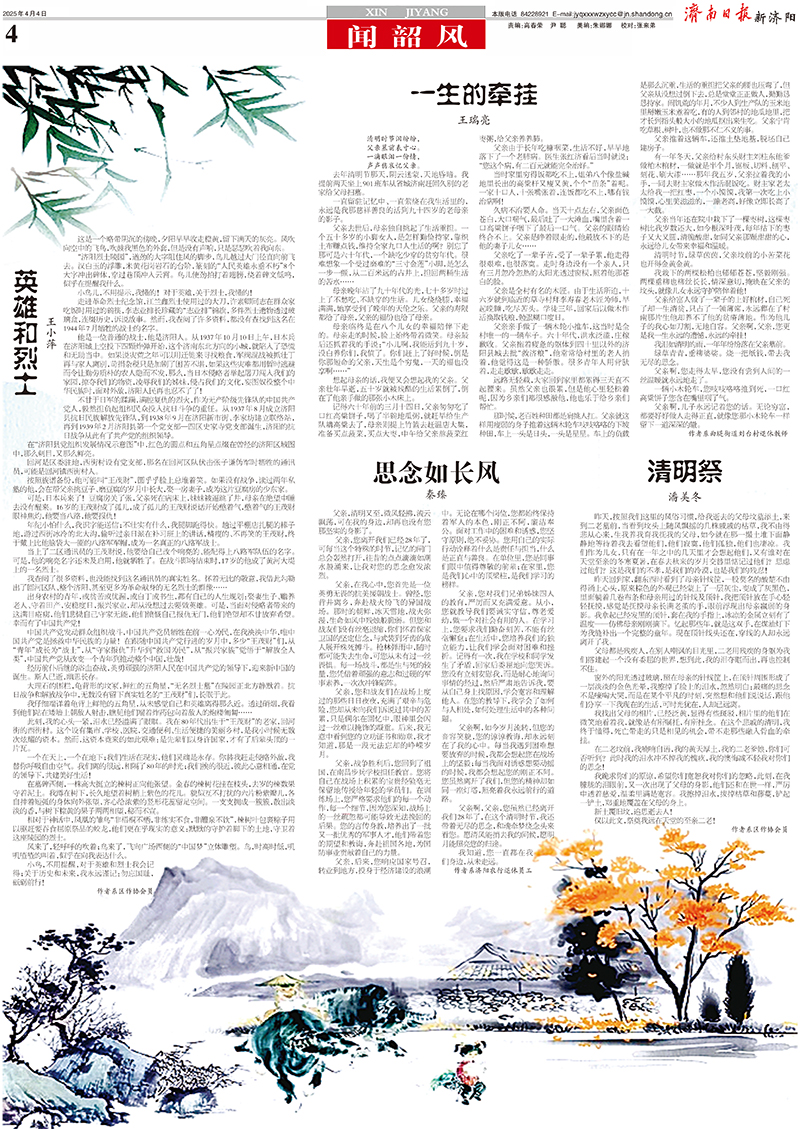一生的牵挂
王瑞亮
清明时节泪纷纷,
父亲墓前表寸心。
一滴眼泪一份情,
声声伤哀忆父亲。
去年清明节那天,阴云迷蒙,天地昏暗。我提前两天坐上901班车从省城济南赶回久别的老家给父母扫墓。
一直留驻记忆中、一直萦绕在我生活里的,永远是我那慈祥善良的活到九十四岁的老母亲的影子。
父亲去世后,母亲独自挑起了生活重担。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脚女人,是怎样勤俭持家,靠织土布赚点钱,维持全家九口人生活的啊?别忘了那可是六十年代,一个缺吃少穿的贫穷年代。很难想象一个受过磨难的“三寸金莲”小脚,是怎么一步一颤,从二百米远的古井上,担回两桶生活的苦水……
母亲晚年沾了九十年代的光,七十多岁时过上了不愁吃、不缺穿的生活。儿女绕绕膝,幸福满满,她享受到了晚年的天伦之乐。父亲的寿限都给了母亲,父亲的福份也给了母亲。
母亲临终是在八个儿女的幸福陪伴下走的。母亲走的时候,脸上始终带着微笑。母亲最后还抓着我的手说:“小儿啊,我能活到九十岁,没白养你们,我值了。你们赶上了好时候,倒是你那短命的父亲,天生是个穷鬼,一天的福也没享啊……”
想起母亲的话,我便又会想起我的父亲。父亲壮年早逝,五十岁就被残酷的生活累倒了,倒在了他亲手做的那张小木床上。
记得六十年前的三月十四日,父亲匆匆吃了口红高粱饼子,喝了半碗地瓜粥,就赶早给生产队耩高粱去了,母亲则提上竹篮去赶温店大集,准备买点菠菜,买点大枣,中午给父亲熬菠菜红枣粥,给父亲养养肺。
父亲由于长年吃糠咽菜,生活不好,早早地落下了一个老肺病。医生张红济看后当时就说:“您这个病,有二百元就能完全治好。”
当时家里穷得饭都吃不上,姐弟八个像盐碱地里长出的高粱杆又瘦又黄,个个“苗条”着呢。一家十口人,十张嘴张着,连饭都吃不上,哪有钱治病啊!
久病不治要人命。当天十点左右,父亲面色苍白,大口喘气,最后吐了一大滩血,嘴里含着一口高粱饼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父亲的眼睛始终合不上。父亲是睁着眼走的,他最放不下的是他的妻子儿女……
父亲吃了一辈子苦,受了一辈子累,他走得很艰难,也很落寞。走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,只有三月忽冷忽热的太阳光透过窗棂,照着他那苍白的脸。
父亲是全村有名的木匠。由于生活所迫,十六岁就到临近的草寺村拜李寿春老木匠为师,早起晚睡,吃尽苦头。学徒三年,回家后以做木作活换取钱粮,勉强糊口度日。
父亲亲手做了一辆木轮小推车,这当时是全村唯一的一辆车子。六十年代,洪水泛滥,庄稼歉收。父亲拖着疲惫的躯体到四十里以外的济阳县城去批“救济粮”,他常常给村里的老人捎着,他觉得这是一种骄傲。很多青年人用背驮着,走走歇歇,歇歇走走。
远路无轻载,大家回到家里都累得三天直不起腰来。虽然父亲也很累,但是他心里轻松着呢,因为乡亲们都很感激他,他也乐于给乡亲们帮忙。
那时候,老百姓种田都是肩挑人扛。父亲就这样用瘦弱的身子推着这辆木轮车吱吱咯咯的下坡种田,车上一头是日头,一头是星星。车上的负载是那么沉重,生活的重担把父亲的腰也压弯了,但父亲从没想过倒下去,总是堂堂正正做人,勤勤恳恳持家。闹饥荒的年月,不少人到生产队的玉米地里掰嫩玉米煮着吃,有的人到邻村的地瓜地里,把才长到指头般大小的地瓜抠出来生吃。父亲宁肯吃草根、树叶,也不做那不仁不义的事。
父亲推着这辆车,还推土垫地基,脱坯自己建房子。
有一年冬天,父亲给村东头财主刘柱东他爹做柏木棺材,一做就是半个月,锯板、切料、刨平、刻花、刷大漆……那年我五岁,父亲拉着我的小手,一同去财主家做木作活混饭吃。财主家老太太给我一把红枣,一个小馍馍,我第一次吃上小馍馍,心里美滋滋的,一蹦老高,好像立即长高了一大截。
父亲当年还在院中栽下了一棵枣树,这棵枣树比我岁数还大,如今根深叶茂,每年结下的枣子又大又圆,清脆酸甜,如同父亲那颗甜甜的心,永远给儿女带来幸福和温暖。
清明时节,绿草茵茵,父亲坟前的小苦菜花也开得金黄金黄。
我栽下的两棵松柏也郁郁苍苍,坚毅刚强。两棵垂柳也柳丝长长,情深意切,掩映在父亲的坟头,就像儿女永远守护陪伴着他!
父亲给富人做了一辈子的上好棺材,自己死了却一生清贫,只占了一领薄席,永远葬在了村南那片生他却养不了他的贫瘠薄地。作为他儿子的我心如刀割,无地自容。父亲啊,父亲,您更是我一生永远的遗憾,永远的牵挂!
我泪如清明的雨,一年年纷纷落在父亲墓前。
绿草青青,垂柳婆娑。烧一把纸钱,带去我无尽的思念。
父亲啊,您走得太早,您没有尝到人间的一丝温暖就永远地走了。
一辆小木轮车,您吱吱咯咯推到死,一口红高粱饼子您含在嘴里咽了气。
父亲啊,儿子永远记着您的话。无论穷富,都要好好做人走得正直,就像您那小木轮车一样留下一道深深的辙。
作者系曲堤街道刘台村退休教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