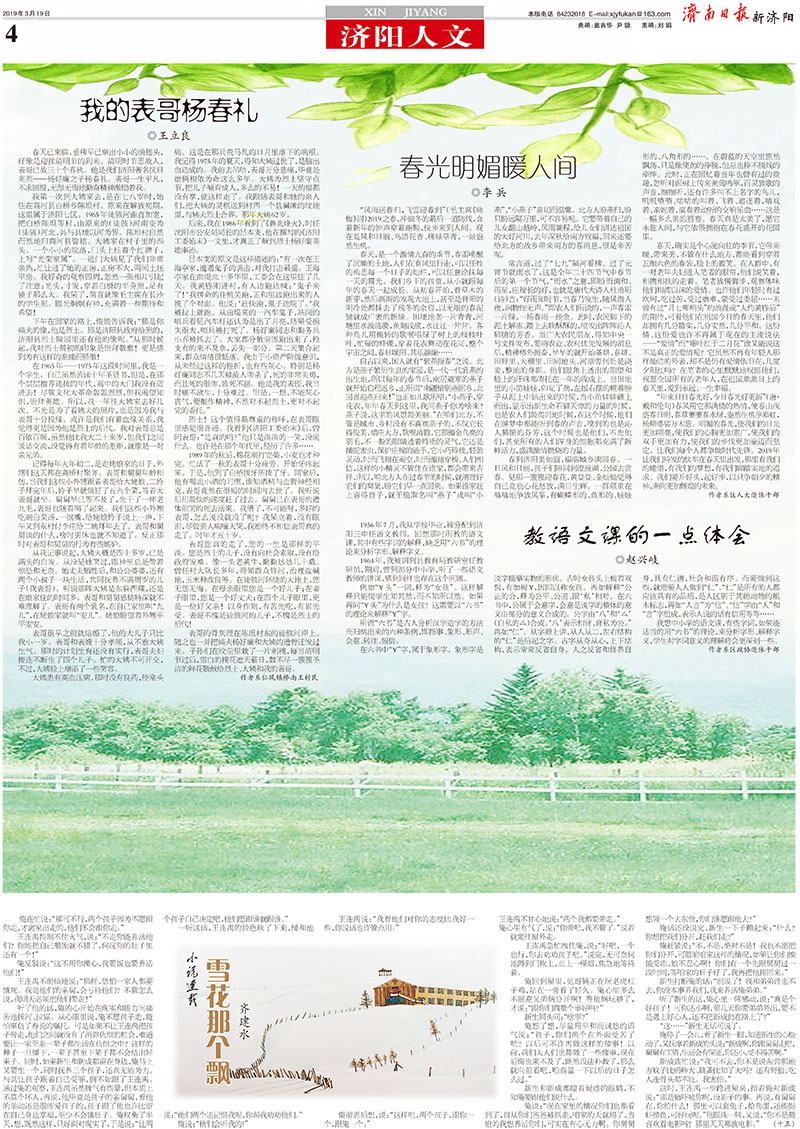我的表哥杨春礼
◎王立良
春天已来临,垂柳早已窜出小小的萌穗头,好像是迎接清明节的到来。清明时节思故人,表哥已故三十个春秋。他是我们济阳著名抗日英烈——杨好廉之子杨春礼。表哥一生平凡,不求回报,无怨无悔地勤奋精神激励着我。
我第一次到大姨家去,是在七八岁时,她住在商河县白桥乡陈坦村。原来在解放初期,这里属于济阳七区。1965年徒骇河曲直加宽,把白桥陈坦等村,由原来的(徒骇)河南变为(徒骇)河北,县与县境以河为界。陈坦村自然而然地归商河县管辖。大姨家在村子里的西头。一个小小的院落,门头上挂着个红牌子,上写“光荣家属”。一进门大姨见了我们非常亲热,忙让进了她的正房,正房不大,两间土坯平房。我好奇的观察四周,忽然一张相片引起了注意:光头,寸发,穿着白褂的半身照,足有镜子那么大。我呆了,简直就像毛主席在长沙的学生照。眼光炯炯有神,充满着一种期待和希望!
下午在回家的路上,俺娘告诉我:“那是你姨夫的像,他是烈士。那是济阳县政府给照的,济阳县烈士陵园里还有他的像呢。”从那时候起,我对烈士最初的印象是崇拜敬慕!更是感到为有这样的亲戚而骄傲!
在1965年——1975年这段时间里,我是一个学生。自己虽然苦读十年圣贤书,但是,在那个层层推荐选拔的年代,高中的大门我没有迈进去!尽管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,但我渴望知识,崇拜英雄。所以,我一年往大姨家去好几次。不光是为了看姨夫的照片,也是因为我与表哥十分投缘。或许是我们有着血缘关系,我觉得更是因为他是烈士的后代。我对表哥总是百依百顺,虽然他比我大二十来岁,但我们之间说话交流,没觉得有着年龄的差距,就像是一对亲兄弟。
记得每年大年初二,是走姥娘家的日子,外甥们这天都在高桥村聚齐。表哥和舅舅年龄相仿,当我们这些小外甥跟着表哥给大姥娘、二妗子拜完年后,妗子早就做好了五六个菜,等着大表哥就坐。舅舅早已等不及了,先干了一杯老九毛,表哥也随着喝了起来。我们这些小外甥吃碗白菜汤,一抿嘴,给姥娘妗子说上一声,下午又到东村付李庄给二姨拜年去了。表哥和舅舅谈的什么,啥时罢休也就不知道了。反正那时对表哥和舅舅的行为有些嫉妒。
从我记事说起,大姨大概是四十多岁,已是满头的白发。从没见她笑过,眼神里总是带着惊恐和无奈。她丈夫牺牲后,和公公婆婆,还有两个小叔子一块生活,共同抚养不满周岁的儿子(我表哥)。听说那阵大姨是东躲西藏,还是在娘家住的时间多。表哥和舅舅感情特深就不难理解了。表哥有两个乳名,在自己家里叫“九儿”,在姥娘家就叫“安儿”。姥娘盼望着外甥平平安安。
表哥很早之前就结婚了,他的大儿子只比我小一岁。表哥和表嫂十分孝顺,从不惹大姨生气。那时的计划生育还没有实行,表哥夫妇接连不断生了四个儿子。忙的大姨不可开交,不过,大姨脸上增添了一些笑容。
大姨患有高血压病,那时没有良药,经常头痛。这是在那兵荒马乱的日月里落下的病根。我记得1975年的夏天,得知大姨过世了,是脑出血造成的。我前去吊唁,表哥万分悲痛,毕竟是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。大姨为烈士坚守贞节,把儿子哺育成人,多么的不易!一天的福都没有享,就这样走了。我跟随表哥和她的亲人们,把大姨的灵柩送到村西一个盐碱滩的坟地里,与姨夫烈士合葬。那年大姨62岁。
后来,我在1986年看到了《鲁北烽火》,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吕本支,他在撰写的《济阳工委始末》一文里,才真正了解到烈士杨好廉英雄事迹。
吕本支的原文是这样描述的:“有一次在王海亭家,遭遇鬼子的袭击,对我打击最重。王海亭家在曲堤北十多华里,工委会在这里住了几天。我黄昏刚进村,有人边跑边喊:‘鬼子来了!‘我拼命的往机关跑,正和里边跑出来的人撞了个对面。他说:‘赶快跑,鬼子进院了。‘我被拉上就跑。从曲堤来的一汽车鬼子,站岗的哨兵看见汽车灯还认为是出了月亮,结果受损失很大,哨兵被打死了。杨好廉同志和勤务兵小乔被抓去了。大家都分散突围跑出来了,枪支有的来不及拿,丢失一部分。第二天集合起来,群众情绪很低落。我由于小资产阶级意识,从未经过这样的挫折,也有些灰心。特别是杨好廉同志不几天被敌人惨杀了,死的非常英勇,而且死的很惨,致死不屈。他是我的表侄,我当时痛不欲生,十分难过。但是,一想,不能灰心丧气,要振作精神,不然对不起烈士,更对不起党的委托。”
烈士!这个值得最尊重的称呼,在表哥眼里感觉很普通。我看到《济阳工委始末》后,曾问表哥:“是真的吗?”他只是淡淡的一笑,没说什么。也许是在那个年代里,经历了许多……
1989年的秋后,棉花刚打完柴,小麦也才种完。忙活了一秋的表哥十分疲劳。开始牙疼起来。于是,他到了白桥拔牙所拔了牙。回家后,他有喝盅小酒的习惯,谁知酒精与血管神经相克,表哥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去世了。我听说后用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。舅舅已在表哥的遗体前哭的死去活来。我懵了,不可能呀,多好的表哥,怎么说没就没了呢?我呆立着,没有眼泪,尽管亲人啕嚎大哭,我始终不相信表哥真的走了。时年才五十岁。
表哥您真的走了,您的一生是那样的平淡。您是烈士的儿子,没有向社会索取,没有给政府发难。像一头老黄牛,勤勤恳恳几十载。曾任村大队长多年,带领群众修河,治理盐碱地,玉米种改良等。在徒骇河环绕的大地上,您无怨无悔。在母亲眼里您是一个好儿子;在妻子眼里,您是一个好丈夫;在四个儿子眼里,更是一位好父亲!以身作则,有苦先吃,有累先受。表哥不愧是徒骇河的儿子,不愧是烈士的后代!
表哥的骨灰埋在陈坦村东的徒骇河岸上。随之也一并把姨夫杨好廉和大姨的遗骨迁发过来。子孙们在坟茔里栽了一片刺槐,每当清明节过后,雪白的槐花遮天蔽日,数不尽一簇簇圣洁的鲜花敬献给烈士、大姨和我的表哥。作者系仁风镇桥南王村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