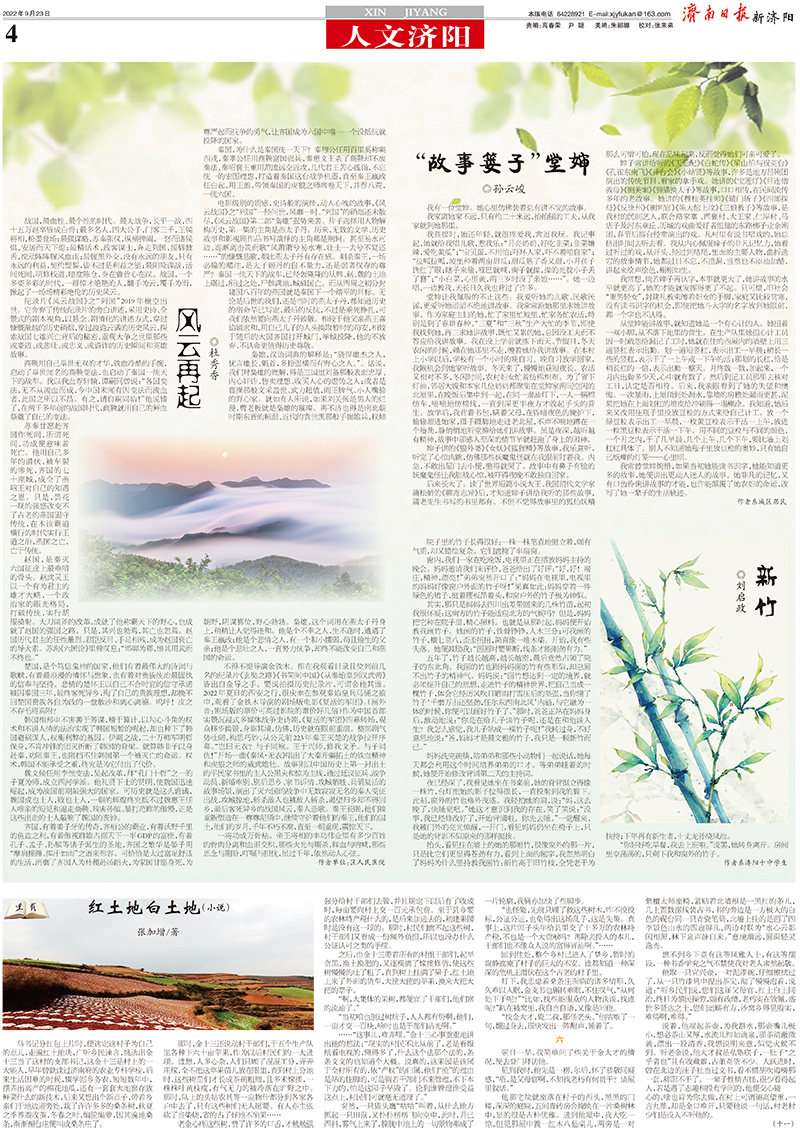“故事篓子”堂婶
◎孙云峻
我有一位堂婶。她心里仿佛装着总有讲不完的故事。
我家离她家不远,只有约二十米远,抬抬腿的工夫,从我家就到她那里。
我孩提时,她还年轻,就很疼爱我,常逗我玩。我记事起,她就给我唱儿歌,惹我乐:“月亮奶奶,好吃韭菜;韭菜嫌辣,爱吃黄瓜”;“宝贝蛋,不用怕;吓坏人家,吓不着咱自家”;“拉呱拉呱,坡里种着两亩甜瓜;甜瓜熟了香又甜,小月孩子馋红了眼;瞎子来偷,哑巴就喊,瘸子就撵,撵的光腚小子丢了簪”;“小白菜,心里黄,两三岁时没了亲娘……”。她一边唱,一边教我,天长日久我也背过了许多。
堂婶让我佩服的不止这些。我爱听她的儿歌、民歌民谣,更爱听她滔滔不绝地讲故事。我常常跑她那里求她讲故事。作为家庭主妇的她,忙了家里忙坡里,忙家务忙农活,特别是到了春耕春种、“三夏”和“三秋”生产大忙的季节,即使我找到她,再三求她讲故事,既忙又累的她,总因没工夫而不答应给我讲故事。我在没上学前就拣下雨天、节假日,冬天农闲的时候,赖在她那里不走,缠着她给我讲故事。在本村上小学以后,学校有一个小时的晚自习。晚自习放学回家,我瞅机会到她家听故事。冬天来了,慢慢地昼短夜长。农活又相对不多,冬闲时间,农村妇女忙着纺棉织布。为了省下灯油,邻居大嫂和本家几位奶奶都聚集在堂婶家两间空闲的北屋里,在晚饭后集中到一起,在同一盏油灯下,一人一辆棉纺车,嗡嗡地纺棉线,一直到深更半夜方才收起手头的营生。放学后,我背着书包,瞒着父母,在昏暗夜色的掩护下,偷偷溜进她家,蹑手蹑脚地走进老北屋,不声不响地蹲在一个墙角,静悄悄地听堂婶给她们讲故事。虽是夜深,越听越有精神,故事中那感人至深的情节早就赶跑了身上的困神。
婶子讲的《狼外婆》《女妖》《狐狸精》等故事,我乐意听,听完了心惊肉跳,仿佛那些妖魔鬼怪就在我跟前盯着我。内急,不敢出屋门去小便,憋得就哭了。故事中有鼻子有脸的妖魔鬼怪让我胆战心惊,被吓得夜晚不敢独自回家。
后来长大了。读了世界短篇小说大王、我国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后,才知道婶子讲给我听的那些故事,蒲老先生书写的书里都有。不但不觉得故事里的狐仙妖精那么可憎可怕,现在品味起来,反而觉得她们可亲可爱了。
婶子常讲给听的《天仙配》《白蛇传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孔雀东南飞》《井台会》《小姑贤》等故事,许多是地方吕剧团演出的传统节目、看家的拿手戏。她讲的《宝莲灯》《目连僧救母》《铡美案》《狸猫换太子》等故事,口口相传,在民间流传多年的老故事。她讲的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辕门斩子》《四郎探母》《反徐州》《铡判官》《陈大倌上坟》《三娘教子》等故事,是我村的民间艺人,联合路家寨 、西蒯村、大王家、仁岸村、马店子及河东章丘、历城的戏曲爱好者组建的东路梆子业余剧团,春节后搭台经常演出的戏。凡村里有说书唱戏的,她总挤出时间去听去看。我从内心佩服婶子的非凡记忆力,她看过听过的戏,从开头、经过到结尾,里面的主要人物,曲折迭宕的故事情节,她都过目不忘,不遗漏,当然也不添油加醋,讲起来绘声绘色,栩栩如生。
我常想,倘若婶子再认字,本事就更大了,她讲故事的水平就更高了,她的才能就发挥得更了不起。只可惜,旧社会“重男轻女”,封建礼教束缚着妇女的手脚,家庭又比较贫寒,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,即使把她斗大字的名字放到她眼前,都一个字也不认得。
从堂婶能讲故事,就知道她是一个有心计的人。她扭着一双小脚,从不落下地里的营生。在生产队里她担心计工员因一时疏忽给漏记了工时,她就在住的西屋内的墙壁上用三道竖杠表示出勤。划一道短竖杠,表示出工一早晨;稍长一些的竖杠,表示干了一上午或一下午的活;那划的长杠,恰是稍长杠的一倍,表示出勤一整天。月终数一数,加起来,一个月内出勤多少天,心中就有数了。然后到记工员那里去核对工日,认定是否相符。后来,我亲眼看到了她的失望和懊悔。一次暴雨,土屋顶到处漏水,靠墙的房檐处漏雨更甚,泥浆把她在上面划杠的墙皮给冲刷得一塌糊涂。我知道,她后来又改用往瓶子里投放豆粒的方式来给自己计工。放一个绿豆粒表示出工一早晨,一枚黄豆粒表示干活一上午,放进一粒黑豆粒表示干活一下午。用不同的豆粒与不同的颜色,一个月之内,干了几早晨、几个上午、几个下午,要比墙上划杠杠具体了。别人不知道她瓶子里放豆粒的奥妙,只有她自己纸糊的灯笼——心里明。
我常替堂婶惋惜,如果当初她能读书识字,她能知道更多的故事,她便讲出更动人迷人的故事。她非凡的记忆,又有口齿伶俐讲故事的才能,也许能颠覆了她农妇的命运,改写了她一辈子的生活轨迹。
作者系城区居民